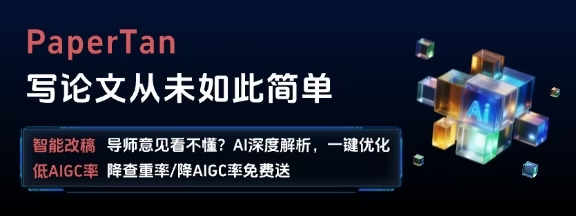创伤叙事的符号化转译:论余华《活着》中苦难记忆的解构与重构
作者:佚名 时间:2026-01-22
本文以余华《活着》为研究对象,探讨创伤叙事的符号化转译对苦难记忆的解构与重构。通过拆解创伤记忆、搭建符号系统、重组叙事话语三个步骤,将零散创伤体验转化为有逻辑的叙事文本。运用重复手法、情感剥离策略及符号能指漂移,把宏大历史苦难转化为日常符号,实现创伤记忆的重构。研究为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苦难书写提供案例,也为文学与历史、个体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第一章引言
《活着》里面创伤叙事进行符号化转译,其理论方面的内涵还有实践方面的意义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创伤叙事属于文学研究里重要的一个方向,它说的是个体或者群体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之后,依靠语言符号重新去构建创伤记忆的心理以及文学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把原本零散、没有理性的创伤体验转变成有逻辑、容易读懂的叙事文本,这样就能够实现心理疗愈以及历史反思这两种效果。在余华所写的内容中,主人公福贵一生所经历的苦难被做了符号化处理,完整地展现出创伤记忆从被压抑到得到释放、从被解构到被重构这样的变化轨迹。
符号化转译具体操作有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把创伤记忆拆解,作者采用非线性叙事方式以及多重视角,打破传统的线性时间框架,让创伤事件脱离原本的时空逻辑,呈现出零散的状态。第二步是搭建符号系统,通过像土地、老牛这类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把抽象的苦难转化成具体的符号载体,给创伤经验增添文化象征方面的内涵。第三步是对叙事话语进行重组,运用朴实克制的语言风格以及重复的修辞手法,完成对创伤记忆的整合与提升,形成独特的叙事感染力。这个转化过程不但体现出文学创作的技术要求,还突出了创伤叙事在文化记忆传承当中的重要地位。
从实际意义来讲,研究《活着》的创伤叙事能够为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的苦难书写提供典型的案例。符号化转译是一种有效的叙事方法,它既可以避免直接描写创伤而带来审美疲劳,又能够通过象征手法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这种叙事模式的价值在于,它给作家处理历史创伤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创作方法,也给读者解读创伤文本提供了清晰的认知途径。深入分析《活着》创伤叙事的符号化特征,不但能够帮助更深入地理解余华的创作美学,还能够为探讨文学与历史、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通过对《活着》创伤叙事符号化转译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到其在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文学作品中创伤表达以及相关理论关系的大门,让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去认识文学与现实、历史与记忆等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联系。
第二章苦难记忆的叙事策略:作为符号的创伤
2.1重复与消解:从历史苦难到日常符号的转化
图1 重复与消解:从历史苦难到日常符号的转化
余华在《活着》叙事安排中用重复手法,把宏大历史苦难变成能感知的日常符号,完成创伤记忆符号化转译。这一转化关键是借助索绪尔符号学里能指与所指关联,将特定历史阶段集体创伤重新编码成有普遍意义的日常行为符号。
以“大跃进”饥荒为例,余华没直接刻画宏大历史悲剧,而是把那段苦难具体为福贵一家“吃观音土”的日常举动。“吃观音土”这个行为作为能指,它指向的所指不再是单一历史事件,而是饥饿时人类求生本能反应。当反复展现“吃观音土”这个行为符号,苦难的历史属性逐渐被剥离,沉重感在重复日常描述中被淡化,最终变成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符号。
在处理“文革”这类政治运动带来的创伤时,余华采用类似符号转化方法。他把复杂政治斗争简化成“开会”“批斗”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动作符号。随着这些符号在故事里不断出现,原本的政治含义慢慢变弱,“开会”“批斗”成了福贵日常生活里躲不开的例行程序。经过这样处理,历史苦难从宏观政治叙事落实到微观个体经验,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历史压迫,而是个体在具体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福贵拉牛耕地的动作、反复哼唱的歌谣等日常符号,让这种转化效果更加明显。这些日常符号不断出现,它们不仅构成了福贵生命的节奏,还悄悄化解了苦难的尖锐程度,让苦难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
表1 《活着》中苦难记忆的重复叙事与符号消解
| 重复叙事场景 | 历史苦难维度 | 日常符号转译 | 消解机制 |
|---|---|---|---|
| 家珍的咳嗽声 | 贫困与疾病的历史创伤 | 生存韧性的日常隐喻 | 以身体痛感的重复性强化生命的持续在场 |
| 福贵的“活着”口头禅 | 个体对时代暴力的无力抵抗 | 生命意义的简化符号 | 以口语化重复消解宏大苦难的沉重性 |
| 土地的耕种动作 | 乡土中国的历史命运 | 存在本质的日常仪式 | 以劳动的重复性消解历史的荒诞性 |
| 死亡事件的循环 | 时代灾难的集体记忆 | 生命脆弱的日常证明 | 以死亡的重复性消解悲剧的崇高性 |
从历史苦难到日常符号的转化,本质是叙事上的解构与重构。通过运用重复手法,余华把原本历史属性很强的创伤记忆,变成了一系列能够被识别、能够被接受的日常符号。这些日常符号既带着苦难的痕迹,又凭借其日常性淡化了苦难的沉重感,最终实现了更深刻的艺术表达。这种叙事策略既符合文本对实践性的要求,又在文学创作中提供了处理创伤记忆的有效办法,体现出日常符号在重构历史叙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2情感剥离:福贵叙事中的零度情感与符号指涉
余华的《活着》采用一种叙事策略,把情感剥离作为实现苦难记忆符号化转译的核心方法。这种策略有主要特征,即叙述者福贵在回忆个人创伤经历的时候,不会直接抒发主观情感,而是用近乎冷静客观、如同“零度情感”的语气,按照事情发生顺序慢慢陈述事实。它的关键原理是抑制情感直接流露,而不是让读者过多投入对苦难事件的共情,目的是让读者注意力集中到事件本身具备的那些符号要素上,把个人内心深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痛苦,转化成具有公共属性、能够被大众解读的外在符号。
这一策略在福贵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内容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当讲到亲人离世这种令人痛苦的时刻,福贵的语言表现得极为克制。就像说到有庆因为抽血而去世,他并没有过多去描述自己内心的悲痛或者愤怒之情,只是用“有庆的脸色就像纸一样白,没多久就没了”这样简短的句子,简单地把生命慢慢消逝的整个过程描述了出来。再比如讲述凤霞难产死亡的时候,叙述重点没有放在产妇承受的巨大痛苦或者家属陷入的深深绝望上,而是集中描述“医生满头大汗”“血染红了床单”这些具体又细微的场景情况。这样的叙述方式把事件原本该有的强烈情感都去掉了,最后只留下事件的主要事实内容和一些细节信息。
情感剥离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把抽象存在的死亡概念转化成可以具体看到的符号指代。在福贵的讲述当中,“死亡”不再仅仅意味着生理上的终结这么简单,而是被转化成“埋在村西头的坟头”“坟头长了草”这类能够被人实际看到的符号。这些符号摇身一变,成了苦难记忆的物质载体,而且它们不会受到叙述者当时心情状态的影响,会以一种稳定不变的形式融入到符号体系里面去。通过这样的办法,个人短暂出现的悲伤情绪被过滤掉,而苦难的本质则被固定在这些稳定存在、能够重复去描述的符号当中。
表2 福贵叙事中零度情感场景的符号指涉分析
| 叙事场景 | 零度情感表现 | 符号指涉维度 | 苦难记忆的解构/重构指向 |
|---|---|---|---|
| 家珍病重离世 | 平静叙述“家珍死得很好”,无过度哀恸描写 | 生命终结的日常化符号、死亡焦虑的消解符号 | 解构死亡的悲剧性,重构生命韧性的日常表达 |
| 有庆被抽血致死 | 以“抽血”动作重复替代情感爆发,仅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了” | 体制暴力的隐喻符号、个体价值消解的符号 | 解构权力压迫的直接控诉,重构苦难的荒诞性认知 |
| 凤霞难产死亡 | 聚焦“医生接生”的机械过程,未渲染悲伤,只提“凤霞也死在了这间屋里” | 医疗伦理缺失的符号、女性生命脆弱性的符号 | 解构生育悲剧的煽情化书写,重构历史语境下的生命失重感 |
| 二喜被水泥板砸死 | 简洁陈述“二喜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无情绪渲染 | 生存环境残酷性的符号、底层命运随机性的符号 | 解构意外死亡的戏剧化冲突,重构苦难的日常性本质 |
| 苦根吃豆子撑死 | 平静说“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未加抒情 | 生存资源匮乏的符号、生命延续的悖论符号 | 解构贫困悲剧的道德化批判,重构苦难记忆的本真性呈现 |
情感剥离策略的实际作用很大,它能避免记忆在反复讲述的过程中出现情感失真或者夸张的情况。要是有过多情感表达,很容易让苦难故事变得像戏剧一样充满戏剧性,反而会降低故事的真实感。而采用零度情感叙事方法,保持一定的叙述距离,就可以让苦难记忆保留住原本具有的真实感,能够让读者越过情感的表面现象,直接触及到苦难本身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到这种冷静的符号化表达,不仅仅加强了苦难记忆具备的客观特性和普遍特性,更加让福贵个人遭遇的生命悲剧变成了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去承受苦难、如何在苦难中生存下去的寓言故事,极大地扩展了文本可解读的空间范围和其中蕴含的思想深度。
2.3符号能指的漂移:苦难在个体生命史中的重构
图2 符号能指的漂移:苦难在个体生命史中的重构
理解《活着》里苦难记忆的重构过程,符号能指的漂移是重要机制。符号能指的漂移这个概念来自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它说的是符号的能指不会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的延续以及意义的差异变化而不断地移动。在福贵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苦难的符号意义正是依靠这种漂移被拆解之后又重新进行塑造。小说里“活着”“牛”“土地”这些核心符号,它们的能指在福贵人生的不同阶段有着明显的变化轨迹,通过这样的变化形成了他独有的生命叙事符号体系。
“活着”这个符号的能指漂移十分具有代表性。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活着”是福贵作为地主少爷身份的能指,它和享乐、奢靡密切相关,成为了他挥霍无度行为的一种符号。后来家道衰败,并且他还经历了战争,“活着”的能指开始发生移动,变成了纯粹的生存本能的符号,代表着在饥饿和暴力的环境里艰难维持生命的那种挣扎。等到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之后,“活着”的能指又一次发生移动,升华成为和老牛作伴的生命韧性的符号,它不再是被动地忍受,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带着对逝去亲人的记忆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这种变化是由福贵个人生活里发生的事件推动的,特别是亲人接连去世这样的事件。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去掉了“活着”原本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迫使它的能指向更加内在、更具精神性的层面移动。
“牛”和“土地”的符号能指也经历了类似的重构过程。“牛”最开始是作为生产工具的能指,后来它和福贵一起变老,变成了苦难当中伙伴的象征,到最后成了福贵生命意志的投射符号。“土地”从代表财富和身份的私有财产,逐渐移动到成为提供生存依靠的物质基础,最后变成了承载所有生命和死亡的终极背景,是福贵接受苦难、回归根本的象征。这些符号的能指不断地移动,使得宏大叙事里的集体创伤记忆,转变成为福贵个人的生命体验。苦难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或者历史符号,而是通过“活着”“牛”“土地”这些具体的符号转换,重新构建成为关于忍耐、温情和存在的个人生命哲学,最终形成了超越创伤的独特叙事模式。
第三章结论
对余华《活着》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可发现创伤叙事的符号化转译在解构与重构苦难记忆方面有着核心作用。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借助文学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将个体难以言说的创伤体验转化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文本。创伤体验通常以碎片、非线性的形式隐藏在记忆深处,符号化转译会挑选特定的意象、情节以及语言结构,把这些碎片重新组合起来,使它们具备逻辑和意义。这种转译不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叙事方法,更是心理层面的一种疗愈方式,能让作者和读者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完成对创伤的审视与超越。
实现这个路径的操作步骤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提炼和筛选创伤材料,作者从原始记忆当中挑出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者情感片段,例如福贵遭遇的家破人亡、饥荒病痛等,这些都成了叙事的原始素材。第二个阶段是构建符号系统,把现实里的苦难转化成象征性符号,就像老牛象征着坚韧的生命意志,反复出现的死亡场景暗示着苦难的循环,如此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编码体系。第三个阶段是重组叙事结构,采用非线性的时间叙事以及平淡的语言风格,打破传统悲剧那种激烈的冲突,用克制的方式来展现苦难,进而完成记忆的重构。这个过程不仅消解了苦难的直接冲击,还重新构建出其对生命意义的深刻启示。
在实际应用当中,创伤叙事的符号化转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学术角度来讲,它为当代文学中苦难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社会学批评,而是转向叙事学和符号学的交叉视角。从实践角度来看,这种转译机制表明文学创作是怎样通过符号化处理个体创伤,让其变成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载体。对于专科阶段的文学研究而言,掌握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深入理解文本的深层结构,提高文本解读的准确性和系统性。与此同时这个分析路径还为其他类似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模式,体现出文学研究从感性体验朝着理性分析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