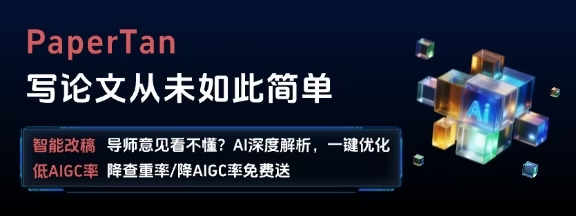创伤叙事的伦理边界与审美重构——以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中心的理论阐释
作者:佚名 时间:2025-12-25
本文以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核心,探讨创伤叙事的伦理边界与审美重构。结合创伤理论与叙事伦理,分析文学再现创伤面临的见证、消费、符号化等伦理争议,指出需平衡真实与艺术。余华通过克制叙事、生存韧性书写(《活着》)与身体创伤-家庭伦理辩证呈现(《许三观卖血记》),实现从“残酷”到“温情”的审美转向,既坚守伦理底线,又以独特手法将创伤升华为生命哲思,为创伤叙事提供了伦理与审美平衡的典范,兼具个体疗愈与历史见证价值。
第一章 创伤叙事的理论基础与伦理困境
1.1 创伤理论与叙事伦理的核心概念界定
创伤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创伤体验的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做系统性的解释。从心理学方面看,创伤通常指经历或目睹极端事件后形成的深层心理伤害,其主要特征有记忆碎片化和延迟反应。弗洛伊德在研究歇斯底里症的时候发现,创伤记忆常常以非线性方式反复干扰当下意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这种临床特征揭示出了创伤的内在结构。拉康从精神分析角度进一步提出,创伤是主体符号秩序里的断裂点,没办法完全融入个体的认知框架,所以具有“不可言说性”。而这种理论困境恰恰凸显出叙事的重要性,通过语言去重构事件顺序,叙事成为创伤主体尝试恢复时间连续性以及自我认知的关键途径。
叙事伦理关注的是叙事行为本身包含的道德方面。凯罗尔·史密斯在《叙事伦理》中提到,叙事不只是意义传递的过程,更是构建伦理关系的过程。创作者书写创伤时面临双重伦理责任,一方面要忠实于历史真相,另一方面要尊重创伤主体的隐私和尊严。这种责任体现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例如采用适度距离的叙事视角或者隐喻性表达,这样做既能够避免对创伤造成二次伤害,又可以保持文本的批判力量。对于读者而言,接受创伤叙事也是一种伦理实践,需要通过共情式理解参与到创伤的见证过程中,进而形成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伦理三角互动。
创伤理论和叙事伦理存在内在联系,叙事既是创伤的病理表现,也是其疗愈的伦理路径。当创伤没办法通过直接陈述来表达时,文学叙事通过虚构与真实相互交织的方式,为创伤提供了能够被理解的符号载体。这种叙事转化过程本质上具有伦理性,它要求创作者在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去寻求平衡,在暴露痛苦和保护尊严之间把握好尺度。余华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作品借助冷静克制的叙事策略,既呈现出历史的暴力创伤,又避免陷入苦难消费的伦理陷阱。所以,研究创伤叙事需要以理论互构作为基础,要把握创伤的心理机制,同时也要审视叙事行为的伦理维度,如此才能够准确理解文学见证历史的复杂价值。
1.2 文学再现创伤的伦理争议:见证、消费与符号化
文学再现创伤必然会涉及复杂的伦理争论,核心问题是怎样把握真实呈现和艺术加工之间的分寸。创伤体验既独特又有极大冲击力,文学用语言描绘这种极端经历时,必然会碰到见证是否有效的问题、面临消费异化的风险,还会遭遇符号化带来的伦理难题。
见证是创伤叙事的开端,也是伦理争议的核心。文学中的见证要求作者尊重创伤者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肩负起为沉默者发声的社会责任。这两种责任存在矛盾,详细描写可能再次伤害幸存者,描写过于克制又可能使历史真相被遗忘。普里莫·莱维对奥斯维辛的书写很能体现这种矛盾。作为经历者,他多次提及语言在描述极端处境时是无力的,认为任何叙述都难免会简化甚至偏离最初的创伤体验。由此可见见证者的伦理困境,既想尽量完整地保留记忆,又不得不承认文学表达存在天然局限。这种局限并非简单的技巧问题,而是人类认知和语言能力在面对极端创伤时存在的根本不足。
在消费主义环境里,创伤叙事有被异化的风险。当创伤故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原本的震撼力可能逐渐变成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文化商品。市场规则会挑选出那些具有戏剧性的创伤片段,将它们包装成符合读者期待的精神消费品。网络文学里的“虐恋”叙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其中的创伤描写常常脱离真实的历史背景,变成刺激感官的叙事材料。这种消费倾向不仅会降低创伤的历史严肃性,更有可能把他人的苦难当作工具,使其成为读者宣泄情绪或者获得道德优越感的途径。因此伦理批评会质疑,当创伤叙事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时,是否在默许一种新的精神暴力。
符号化是创伤叙事遇到的另一个伦理方面的难题。为了让作品更有普遍意义,作家常常需要把具体的创伤提炼成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学意象,然而这个过程可能会让原本的痛苦体验变得抽象。在处理集中营题材时,有些作品喜欢使用焚尸炉、毒气室这类高度符号化的意象,反复使用会慢慢降低这些历史符号的冲击力,使它们变成可以随意挪用的文化符号。更深层次的风险是,当创伤被过度符号化,读者可能只关注象征意义,却忽视了背后真实的历史个体。这种“意义的溢价”最终会与创伤叙事的初衷相违背,本来是想让被遗忘的人重新发出声音,结果可能导致创伤本身陷入另一种被遗忘的境地。文学需要在保持艺术表现力和尊重创伤真实性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不仅仅是对创作者伦理智慧的考验,也是评判创伤叙事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章 余华小说中的创伤呈现与审美策略
2.1 《活着》:历史暴力下的个体创伤与生存韧性的书写
《活着》按照福贵的人生轨迹来展开情节,它把个人所经历的伤痛与20世纪中国历史里的暴力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创伤书写模式。小说当中的创伤呈现出多个不同的维度,这里面既有亲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开所带来的情感方面的伤痛,也有社会处于动荡状态造成的生存危机。福贵原本是地主家的少爷,后来变成了一贫如洗的农民,他命运出现转折的时间恰好对应着土地改革这一历史背景;他的妻子家珍因为过度劳累早早离世,儿子有庆为了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失去生命,女儿凤霞因为难产去世,这些悲剧都和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有着悄然的关联。余华没有把这些伤痛简单地认为是个人命运不好导致的,而是借助福贵的经历,展现出历史暴力是怎样一步一步侵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得个人的伤痛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
在创伤书写中的伦理表达方面,小说采用了克制且真诚的叙事方法。余华没有直接对历史事件作出价值上的判断,而是以福贵的视角去记录伤痛发生的具体过程,保留了伤痛体验最原始的模样。就拿有庆去世的场景来说,小说仅仅描写了福贵看到儿子冰冷的尸体时“腿一软就跪了下去”,这种白描的手法既尊重了伤痛事件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特性,又避开了历史叙事那种宏大的套路。小说通过福贵朴实的自言自语,把抽象的历史暴力转变为能够让人切实感受到的生活体验,这样的叙事方式既守住了伤痛记忆的真实性,又在个人经历和历史之间划分出了伦理界限。
小说最为突出的审美方法是通过生存的韧性将伤痛转化成为审美体验。福贵经历了所有亲人都离开的情况之后,选择和一头老牛相伴生活,这种看起来消极的生活状态之中隐藏着深刻的生命哲理。余华运用第一人称回忆的方式来进行叙事,让老年福贵用平静的语气讲述过去所经历的苦难,其语言当中带着历经沧桑之后的平和。当福贵对老牛说“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天,苦根也累了,家珍、凤霞耕得少些”,把亲人的名字安在耕牛身上的这种叙述方式,既缓和了伤痛所具有的尖锐感,又用富有诗意的方式怀念了已经逝去的人。小说通过福贵和老牛相互依靠的关系,把具有毁灭性的伤痛转变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让生存的韧性成为审美重构的核心内容。这种叙事处理不只是单纯地展示苦难,更在伦理和审美这两个层面,树立起了创伤书写的典范。
2.2 《许三观卖血记》:身体创伤与家庭伦理的辩证关系
图1 《许三观卖血记》:身体创伤与家庭伦理的辩证关系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用细腻笔墨描写许三观身体创伤,以此建立起身体体验和家庭伦理之间的深层联系。小说里卖血不只是造成生理伤害,更成了支撑家庭伦理的重要纽带。许三观多次去卖血换钱来应对各种家庭危机,比如为一乐凑医药费、给儿子准备下乡生活费用等情况。每次卖血都会带来强烈身体痛苦,从最初的头晕乏力到后来身体衰竭,这些创伤被赋予伦理含义,成为父亲责任和家庭担当的具体体现。
身体创伤和家庭伦理之间存在一种辩证互动关系。卖血带来的身体伤害让家庭伦理更具合理性,许三观承受的痛苦被升华为父爱的牺牲精神,使得家庭伦理能在物质匮乏环境中得以维持。而家庭伦理的需求又反过来加重身体受损程度,当卖血从临时应急办法变为家庭生存常态,伦理责任逐渐变成对身体的过度消耗。这种矛盾关系在小说中通过许三观心理变化体现,他从一开始害怕抗拒,到后来变得麻木顺从,最后把卖血当成一种伦理本能。
在审美呈现方面,余华采用了克制且精准的叙事方法。他通过卖血场景中的具体细节进行刻画,像抽血时身体颤抖、喝水时急切、休息时虚弱等,将身体创伤转化为有冲击力的审美形象。并且小说通过许三观内心独白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展现出创伤背后的伦理难题,既体现出传统家庭伦理坚韧力量,也指出其对身体价值的忽视。这种双重视角使小说在展现身体创伤与家庭伦理复杂关系时,既具备伦理反思的深度,又保持了审美表达的张力。
2.3 从“残酷”到“温情”:余华创伤叙事的审美转向与重构
余华笔下创伤叙事有明显变化,早期是“残酷”风格,后来逐渐转向“温情”风格。这种审美层面的调整反映出他创作理念演变,也使对创伤本质的伦理思考更深入。
早期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里,余华用近乎冷淡笔调描写暴力和荒诞,将创伤直接视为单纯的身体疼痛与心理折磨。“残酷叙事”借助零散情节和极端场景,让创伤的冲击感更强烈,使读者陷入无力的绝望之中。随着写作经验增多,余华发现仅摆出创伤无法说清其全部意义,需要进行审美的重新构建,给予创伤超越痛苦的可能。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充分体现了这种转变。在《活着》里,福贵一生充满失去和苦难,但余华没有一直聚焦于痛苦,而是采用缓慢叙述节奏和含蓄情感表达,凸显出福贵在绝境中的坚韧。小说结尾并非传统悲剧模样,福贵与老牛作伴的场景,暗示创伤可能在生命持续过程中慢慢化解。而《许三观卖血记》与《活着》不同,其中直接增添了许多温暖元素。许三观一次次卖血支撑家庭,这些举动既是应对生活创伤,也是守护亲情。余华运用更轻快叙述方式,添加一些幽默小细节,让家庭温暖逐渐冲淡创伤的沉重。如此一来,创伤不再是让人喘不过气的事物,反而成为人物成长的机会。
这种审美变化背后的伦理原因值得深入探究。余华逐渐认识到,描写创伤不能只追求放大痛苦,更要关注其中的人性。《活着》里福贵拼命活着,是对平凡生活价值的肯定;《许三观卖血记》中,家人间的温暖成为对抗创伤的重要支撑。这样的变化表明余华重新思考了生存的意义,即虽然创伤无法避免,但人们通过感情相连、通过生活中的行动,可以赋予创伤新的意义。从讲故事的方法角度看,余华调整叙述节奏、塑造普通却坚强的角色、设计有希望的结尾,这些方法使他在审美上超越了创伤本身。像这两部小说的结尾,都没有停留在悲剧性的死亡或崩溃上,而是引向平静的延续,让读者既感受到创伤的疼痛,又能体会到生命的坚韧。
余华创作创伤叙事,从早期的“残酷”风格转变为后来的“温情”风格,不只是写作风格发生了改变,更是对创伤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通过审美的重新构建,他把创伤从简单的痛苦转变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变化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里的创伤书写,也给读者带来了更积极的伦理启示。
第三章 结论
本文以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作为研究的文本,探讨文学创作中创伤叙事的伦理边界和审美重构问题。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梳理后能发现,创伤叙事并非只是单纯地罗列苦难,而是作家在尊重历史真实和个体尊严的基础之上,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把创伤体验转化成有着普遍人性价值的审美文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创作者要坚守伦理底线,避免出现猎奇式消费苦难的情况,还要建立起审美距离,使得读者能够超越直接的情感冲击,深入细致地思考生命的本质。
从余华的创作实践情况来看,把握创伤叙事的伦理边界,重点在于处理好尊重真实和艺术虚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活着》这部作品里,福贵一生经历了战乱、饥荒以及亲人离世等诸多不幸之事,然而余华一直用克制的笔触来叙述,没有刻意去渲染血腥的细节,而是借助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叙事,呈现出苦难的持续性。这样的处理方式既保持了历史创伤的严肃性,又给读者留出了情感投射的空间。《许三观卖血记》里,重复出现的卖血行为反映出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但余华没有把这一过程简单地当作道德批判的对象,而是展现出人物在极端环境下对尊严的坚守。这种伦理自觉让创伤叙事不会沦为廉价地展示苦难,而是成为人类面对灾难时精神层面的映照。
实现审美重构,主要依靠选择合适的叙事视角以及创新艺术手法。余华采用零度情感的叙事姿态,运用冷静客观的语言风格,消除了创伤叙述中的煽情倾向,让文本呈现出“反高潮”的美学特点。在《活着》中,接连发生的死亡事件被当作生活中的常态来处理,这种去戏剧化的表达反而让悲剧的震撼力得到了增强。在《许三观卖血记》里,重复叙事手法的运用,既凸显了生存困境的循环性,又形成了独特的节奏美感。这种审美转化让创伤体验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升华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哲学探讨。
创伤叙事具有当代价值,它能够为个体创伤疗愈提供文化方面的参考。当读者通过文学作品重构的创伤叙事来反观现实的时候,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情感净化功能,可以帮助读者缓解心理压力。余华笔下的人物处在绝境之中仍然执着于生命,这种精神力量为当代读者应对困境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创伤叙事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它以文学的形式保存集体创伤的真实情况,给后人以警示,避免再次重蹈覆辙。从这个角度来讲,创伤叙事既是一种艺术创造,也是对历史的见证,其中伦理边界和审美重构的平衡点,是衡量文学作品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