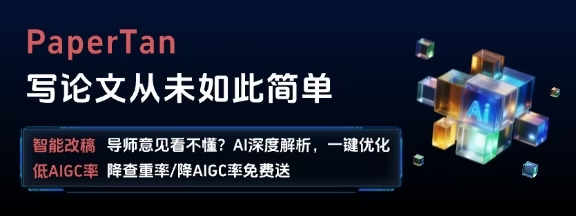数字化的哲学局限与美学悖论
作者:欧阳友权 时间:2007-01-09
在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对其实施价值阐释不仅需媒介认知与技术效益考察,更需人文价值理性的意义探索。本文探讨数字化的哲学局限与美学悖论,旨在揭示技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遮蔽,并借助现象学诠释构建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精神平台。数字标准化限制个性意义体认,平面化处理消弭深度认知,知识化束缚意志自由,这些局限与数字艺术的美学悖论如虚拟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文学在线与文学性消散等,共同构成了科技与人文协调统一的挑战。通过批判性反思,寻求高技术与高人文的和谐共生。
在互联网触角延伸、无远弗届的今天,对数字化技术进行价值阐释,需要的不再是单纯的媒介认知,也不限于技术功能的效益省察,还需要有人文价值理性的意义阐释。探询数字化的哲学局限与美学悖论,旨在破除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遮蔽,将电子媒介革命的现象学诠释作为体认和建设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思维平台和实践前沿,让网络技术的文化命意不断创生与人的精神向度同构的意义隐喻,使其成为人类“澄明的精神在大地行走”的一种生命安顿方式,以求达成高技术与高人文的协调与统一。
一、数字技术的哲学局限
数字化技术显在的技术优势与潜在的哲学局限构成其同时并存的两极。这种哲学局限首先表现为数字标准化对事物个性意义体认的限制。数字化“比特”对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检测与传输是静态的、标准化的,它可能乃至必然抹煞事物背后的内在差异性,消弭视域内所有知识、技能、规则、标准、程度的个性特征。对本原性事物作技术化削足适履,有利于对象的量化处理和规范传输,甚至带来创造性转换和功能的提升,但同时也是对事物潜蕴意义的漠视和背离。例如,正如专家所言“比特不可能测试出组织的功效、文化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它揭示出的只是事件―关系―信息的一个新维度而已。(P8)例如,网络交友的方便快捷,让有情人“e网情深”,然而却难以获得对象个性和人品的真正体认,虚拟的网恋甚至可能使真正的有情人失去幸福。网上写作态情快意、发表自由,让无名者体验到“我也可以当作家”的快感,但降低“作家”的门槛、消除发表作品的限制后,创作成了电子符号的标准化生产,“作家”的速成与速朽、作品的速生与速亡却是互联网本身所无法逆料也无以评判的。网上阅读资源无限、应有尽有,可“读屏”时的图文链接干扰和快餐式填鸭,却让人再也难以悉心品味“读书”时细嚼慢咽的那种隽永的诗意和艺术内视的彼岸性。“比特”对“原子”的阻隔,很难让欣赏者获得文本个性的亲和力,去体察作品“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和“艺术里的精神”(康定斯基)。所以,在数字化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哈贝马斯曾经忠告的:“技术已经使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得以合法化”,他说:“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上,生产力似乎进入了一种与生产关系的新的组合关系。现在,它们己不再为政治启蒙的利益而充当对流行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相反却成了合法性的基础。”(P84)
还有数字的知识化对意志自由的限制。“技术(包括‘网络技术’)导源于‘求知意志’( the wi to know),人文精神导源于‘意志’的自由。因此在技术的时代(即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时代),人容易沦为‘求知意志’的奴隶;而在信仰的时代,人的自由意志被‘无知’所蒙蔽。”(P177)人类求知意志发明的数字化技术提升了知识的价值,甚至诱发“网络为王”的知识崇拜,却又限制了支撑“求知”的意志自由。按照康德的观点,思想为知性提供“意义”,理解则为感性提供“知识”,而互联网的接入和运用主要是基于“知识”――技术知识,而不是“意义”,是出于求知知识,而不是求知意志;不仅不是意志对意义的探寻,还可能导致人们对于意义求知的束缚――因为意义是价值层面的东西,知识则是客观认知的对象,数字化是知识性的工具载体和技术手段,它的炫目与神奇吸引的是求知者的眼球,却遮蔽了知识背后意义的光彩和对价值的意志追求。在互联网上,我们获得的是“知识”,而我们的头脑总是试图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我们生活的意义之所以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头脑里得来,根本原因在于生活的意义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可能被领悟。知识是外在的东西,而意义是内在价值的体认,“意义”的意义在于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置体认主体为度外的“知识”,而在于它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一种理性的沉思,一种意志的洞见,一种入乎其内的价值关怀,这不是靠知识(如数字化知识)的占有所能决定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知识对意义体认主体来说是外在的、非中心化的、非价值主体的,它与意义之间还隔着一条数字化鸿沟,人的求知意志需要迈过这条鸿沟并且把“鸿沟”变作“桥梁”才能真正求知其真正的意义。
有时候,技术的霸权还可能导致“知识至上”,用工具理性解构人文的意义,最终走向价值理性和意志自由的反面。尼采就曾说,现代科技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机械的世界,“而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P256)。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诺(T.Adorno )、马尔库塞(H.Marcuse)、哈贝马斯(J. Harbermas)等人,从社会批判的政治和人文立场对现代技术及其文化工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为什么笛卡尔新科学的“数学宇宙”的理想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噩梦中沦为泡影?为什么在培根、笛卡尔、伽利略所热烈呼唤的新时代里,人类并没有进人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而是沉沦到一种新的野蛮之中?主要原因则在于“技术的解放力量转化为解放的桎梏”,科技构成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铸就了一种新型的以科学为偶像的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造成“理性的黯然失色”(霍克海默)、“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和“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的悖反,因而,应该以“交往旨趣”代替“技术旨趣”,才能使人类“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说,瞩目于技术的知识使现代人成了“一个为了机器平稳运行而被安在某个位置上的东西”,这样,“自由不仅受到各种统治者的威胁,而且更多地受着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控制的东西的支配和对其依赖性的威胁”(P132)。弗洛姆(E.Fromm)说得更尖锐:“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人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为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P25)他提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P96)技术的这些局限衍生出求知意志对求知意义的限制或技术知识对意志自由的束缚,这也许可以说是“科技与人文”的精神现象学在数字化时代所要面对的新的“斯诺命题”①。
二、数字艺术的美学悖论
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是人类理性的伟大创造,但数字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技术性程序和人性化的编码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需要调解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在网络艺术活动中则体现为数字化艺术的美学悖论,对这些悖论的理性反思将使我们在培植科技与艺术共存共荣境界时,持有一份真诚而清醒的诗意关怀。这里拟涉及这样几种观念上的悖论及其对立与统一:
数字虚拟与艺术真实。在传统的艺术美学中,“真实性”是一个艺术价值论、审美意义论的范畴。无论是写实文学的生括真实、浪漫文学的情感真实、象征文学的心理真实,还是荒诞作品的本质真实,都需要一个实存的现实物(人)作为参照系,以便为艺术品确定一个能被主体的知、情、意所认同的评判尺度。然而对数字艺术、特别是网络作品的“真实性”评判却失去了这个主客分立的逻辑前提――数字化网络创作是基于“赛博空间”缔造的“虚拟真实”,它既非客体,也非主体;既是艺术真实的对象,又是艺术真实的本体――网络艺术在表现这一虚拟时,需要借助这一虚拟,同时又是在创造虚拟本身。华盛顿大学的布里肯(W.Briken)对网络虚拟真实的表述是:
心理学是虚拟真实的依据,界面即我们的身体。
知识用经脸来表达,环境中存在着数据。
尺度和时间是探索的坐标,一次经验标价1兆。
要问虚拟真实的含义,就是实实在在已不必要。(P33)
这样的“真实”是虚拟的,但却是真实的,是可以感觉和把握的,它是数字艺术真实生成的背景,达成的是虚拟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它并没有完全摆脱客观现实的认知和参照模式,却又独立于物理现实和心理现实而构成自主性艺术真实。创造“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概念的威廉・吉布森(W.Gibson)在他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解释说:“赛博空间是成千上万接人网络的人产生的交感幻象,……这些幻象是来自计算机数据在人体中再现的结果。”(P67)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有条理的信息构成了一个非物质的虚拟空间;二是身体虚拟化,达成人机合一。(P25-26)这样的赛博空间用虚拟构成真实,又用真实表达虚拟,数字艺术的美学建构就在于从二者的悖反中获得审美创造的张力。
文学在线与文学性消散。数字化互联网首先是作为一种新的载体出现在文学面前的。尽管文学走进网络或者网络接纳文学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选择,但文学“在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文学,而常常是源于游戏、休闲、表达、交流、“孤独的狂欢”等等。此时,文学性(iterariness)不仅可能被遗忘或遮蔽,还将被“祛魅”(disenchantment)和消散。文学的审美原点和价值本体在于其文学性,即如雅可布逊(R.Jakobson)所说的:“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P104)网络文学恰恰是用符码游戏性替代了文学性,用机械复制性替代了文学的经典性。在这里,“文学”是在线的,甚至是簇拥登场、火爆抢滩的,而“文学性”却是飘散的,逃逸的,无以言说的。法国作家吉斯・黛布雷( R .Debray)从媒体特征的角度解释过电子艺术的非文学性和非审美性问题: